《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记 —人生忧患忧思始 王才路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记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记
—人生忧患忧思始
王才路
这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书稿,是我《中国古代小说流派史》和《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的姊妹篇。趁着付梓前的一点时间,我带着一种宽容的心境重新粗读了一遍,但既无如释负重之感,也无什么良好的自我感觉。它毕竟是几年前写成的一部书稿。记得是在1990年9月,我到北京大学做谢冕先生的访问学者。在先生的精心指导下,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精神”的课题研究。在这一课题研究中,我接触到大量的小说研究资料,这是我在我的相对偏僻、资料贫乏的滨海一所高校中难以搜求到的宝贵资料。所以,在紧张的课题研究中,我又挤出一点时间,补写出此前我没有完成的这部书稿中的几章。整个书稿的写成,算来距今已有五年的时间。其中个别章节虽有小修小补,但总体上还是一仍其旧。书稿先后转送几个出版社,又正赶上出版界一声长叹的萧条时节。几声长叹,几声惋惜中,书稿终于遇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终于有机会得以出版。这时候,我已由先前的滨海一所高校到美丽的黄海之滨一所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工作一年多,抚摸着手头的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心潮就激动、思绪翩翩,其中既有奋斗挣扎的精神劳累和肉体消耗,也有过程中虫咬蚊叮的伤痕和烦恼。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当我伏案写作时,窗外蚊蝇拼命地撞进来叮咬。有的竟撞在透明的玻璃上,我知道那几只是瞎了眼的,还有两只花纹腿,人们都说是咬人很凶的母蚊子,其中一只跛了脚的,隔着玻璃便张开吸血的长嘴。我知道,偏僻的地方,有垃圾的地方,是极易生出这种东西来的,几次叮咬之后,我倒也获得了免疫力。现在自然是不至于心了,但想起那时的情形来,心头仍不免一阵悚然之感。我已离开那个地方一年多了,听说那滨海已成了“卫生”城市,听说那些蚊蝇也快寿终正寝了?
我非常怀念那里的十几个年头,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师长和朋友。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多的理解和友情,是我在教书育人之余,写作出版了基本学术专著,主编并出版了近二十部著作,教科书,还有八十万字和四十万字的两部编著,一部近二百万字的大型工具书。我自知才疏学浅,有时在研究对象面前显得那么吃力,那么笨拙,但在师友的热心支持和道义的感召下,我还是执着的进行思考,并努力地把这些思考写出来。它倾注了这些师友们的爱心和友谊。我应当在这里列出一长串他们的名字,以表示我衷心的感谢,然而我又不想借这样一本浅陋的书,去一一亵渎他们的声名。我更愿意把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理解与友谊铭刻在心,时时激励自己,鞭策自己。
我非常怀念在北京大学跟从谢冕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精神”课题的那些时光。我从小就向往着北大,但沉重的岁月让我失去了选择这所学校的机会。我知道,那里是一片圣地,数十年来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智慧,庄严无谓的独立思考以及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和勇锐的抗争精神,成为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九十年代初偶然之机,我已访问学者的身份踏进了这所庄严神圣的校园,而且跟从一代宗师谢冕先生学习和研究,心头也不免升起了庄严感、荣耀感,但更多的感到的还是一种人生忧患的沉重。伴随着学习和研究,更加感觉到这沉重的分量。我经常到先生的家去,先生也经常约我到他家做客,而且有一次竟然喝的是先生珍藏了很长时间的绍兴状元红,据说那酒已在地下埋了很长很长时间。打开盖,顿时满屋溢香,未饮先醉。我至今似乎还置身在那醉人的美景里。酒醇不过是媒介,不过是溢香的有灵魂的水。我动情地望着先生和师母陈素琰女士,一代宗师超人的智慧,哲人的思考,诗人的气质,横溢的才华,如珠的妙语,至今虽已时过五年,但我仍仿佛置身其中。更令我难忘的是,我按照先生的要求,详细的列出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精神”的详细提纲,先生尽心改过,把我叫去,逐一地和我“商讨”,一边详细的询问着我关于某章某节的思路,一边滔滔不绝的发表着他的想法和看法。其中既有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思考,也有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预测和展望。那种机智,那种聪慧,那种灵气,那种洒脱,那种激情,那种活力,是我平生所少见得到的。从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
我不能忘,1991年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毕业答辩论文,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邀请同行专家审评。当时邀请了缪俊杰、乐黛云、王富仁、骆寒超、郑敏、陈丹晨、童庆炳诸位先生,竟然也破例邀请了我。我诚惶诚恐,不敢接受,但后来终于还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接受了这种雅意。因为我知道,先生始终在寻找并创造机会和条件,恨不能一下子使我走出少年。在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我不仅完成了预定的课题,也完成了这本书稿。当我把这本书稿清样寄给先生,先生于百般忙碌之中抽出时间仔细看过,有亲笔写了序言。当我接到序言时,见字如人,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以及我们或彻夜长谈,或轻松漫游,或燕斋小酌的诸多情景,都一一浮上心头,顿时沉浸在一片幸福的回忆中。如今已是五年过去了,至今我的床头上方,依然珍藏着先生书赠的一副条幅,浸透了先生的一片爱心。在我的相册里,还珍藏着与先生的合影。先生坐在我的身边,微笑着摆着姿势,似乎仍然在谆谆教诲着我……
我更不能忘记业师朱德发先生。二十年来,他始终如一,一直无私地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在我的一些文章和书稿中,在我的成长和前进道路中,都浸透了先生的大量心血。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写作这部书稿时,我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借鉴了同行们的许多成果,除了在文中一一注明一些文章外,我在书末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参考书目单,以表示我对他们真挚的谢意。我要感谢出版社的杨乡桥女士,他对这本书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还要感谢主管科研工作的杨富民副校长,以及科研处的宋老师等人,经过慎重考虑,他们答应将此书列入于维紘学术出版基金。北京大学孙庆升教授、烟台大学丁金国教授曾审阅此书,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丁金国教授还多次过问此书的出版情况。其善爱之心,奖掖之情跃然纸上,藏我心中。总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书稿肯定存在着很多问题,我期待着同行和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王才路
1995年8月18日于黄海之滨




上一篇:《唐宋词流派研究》序 王才路
最新更新
- 中國傳統節日的東夷文化成因、發展及當代IP形塑和傳播 (下)王才路[ 於 蕾[
- 中國傳統節日的東夷文化成因、發展及當代IP形塑和傳播 (中)王才路 於 蕾
- 中國傳統節日的東夷文化成因、發展及當代IP形塑和傳播 (上) 王才路 於 蕾
- 归帆携雨,文光射斗犹带伤痕泪 探海骊珠,笔力擎天仍是赤子心 ——乾成书院里的一场文学盛宴 王才路
- 气驱腕使金钢杵 笔歌墨舞抒情怀 —浅谈张宝珠先生的山水画 王 才 路
- 沽河三百里种粮种树都是种诗,仓廪八千座寻流寻源都是寻道 ——春泥诗社东鲁仓都诗歌采风随想
- 遊园无题 王才路
- “拜水丽江问道云南研学行”有感 乾成书院 韩建云
- 壬午1400年祭 ——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夏王窦建德的文化叩探 (之二) 作者 王才路
- 壬午1400年祭——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夏王窦建德的文化叩探(之一)作者 王才路
推荐阅读
关注我们


 乾成书院
乾成书院  师生诗文创作
师生诗文创作  直播研究院
直播研究院  乾成书画院
乾成书画院  大沽河研究院
大沽河研究院  党建品牌研究
党建品牌研究  大沽河书院
大沽河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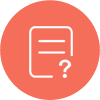 王才路文化品牌研究
王才路文化品牌研究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